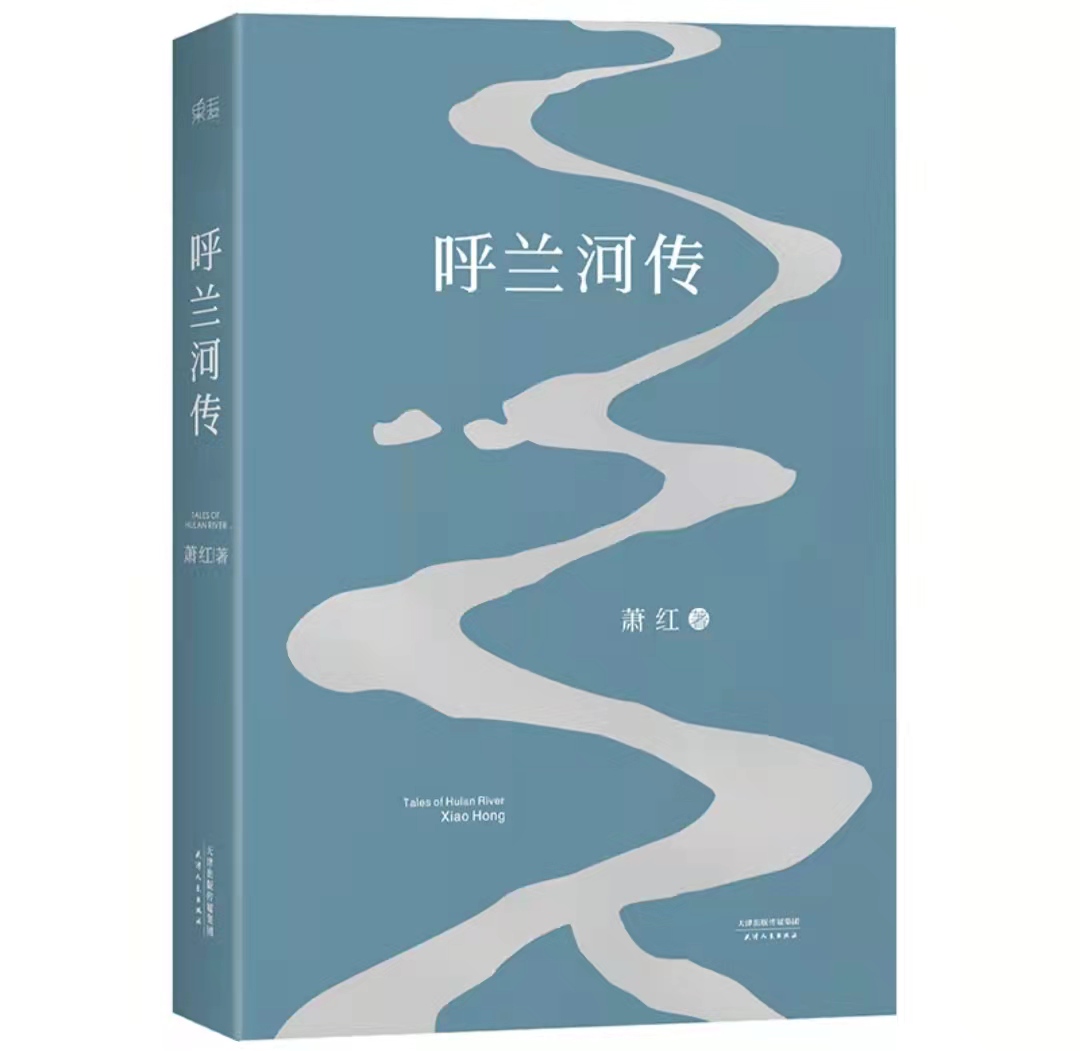星与月光不解悲
——《呼兰河传》
作者简介: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本名张秀环,后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长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作品简介:《呼兰河传》是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该作品于1940年9月1日见载于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12月20日,萧红于香港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创作,12月27日全稿连载完。该作品以萧红自己童年生活为线索,把孤独的童年故事串起来,形象地反映出呼兰这座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从而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成的毒瘤,以及这毒瘤溃烂漫浸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
闲谈:季羡林在《我的童年》中写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在这一片浓稠的黑暗中,就有萧红在东北黑龙江省的呼兰河城里度过了她的童年。
一、呼兰城的美
呼兰城是一座原始的农村小城,它封闭着形成一个小小的生态圈,在里面上演着属于它的人情世故,四季冷暖。这样的小小的生态圈,几乎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每个城镇生活的缩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生命的思考,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几个人、几匹马、几条狗从生到死的重复。
也许它是美的。
毕竟小小城镇透露着它的、它里面人们的纯粹质朴。街道上的店铺不需要显眼的招牌,只要一个“盐”字,两张布幌子就是最好的招牌,甚至药店都可以直接以医生的名字命名。小小的城镇不过就那么几条街道,城里人、乡下人都把这几条街道熟记于心,都是认准了的,用不着什么招引方式。“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大家都平静的过着日复一日的名为“生存”的日子,也会期待为生活带来些乐子的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庙会……这些被称为小城镇住民的“精神盛举”,每一项盛大的仪式背后都牵连着几位牛鬼蛇神,也是人借着“神”的光完成一些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那夜静时分的雨丝中送神归山的鼓,从上流拥拥挤挤浮下来打碎月亮倒影的河灯,戏台子下迎接远嫁归来的女儿的母亲和春心萌动的少男少女,从庙会上带回家的头发被挤没了的不倒翁,都是小民们向鬼神们揩油借光的证据,也确实是那个年代封闭落后中不可多得的快乐。
“漫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但它美也没有多美,美里也透着悲凉。
二、呼兰城的丑
它有着无法隐瞒的丑。
潮湿氤氲的乡土气息中混杂着愚昧、迷信、冷漠和最原始的恶。东二道街上有个淹死不少动物、给人们出行带来不便的泥坑,年复一年的干了又湿,人们抱怨着它惹出的乱子,却没有人把它填平。青一块紫一块的瘟猪肉也有着广阔的市场,因为人们自欺欺人的说:“那猪也许不是瘟死的,是泥坑淹死的。”染缸房、扎彩铺、卖烧饼的、卖麻花的……每个胡同小巷发生的关于生老病死的事,都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成为街坊邻居的谈资。小民们按部就班的为生计奔波着,忙里偷闲时互相议论东家长西家短,没人在乎故事里的主人公当下的生死与感受,甚至有时谈论猪鸭的生死都要比讨论人的生死有感情些,毕竟每一位小民都不确定自己明天的生死,他们只为自己的生存着想。
贫穷和封闭让那个时代下的城镇小民们的生活乏味落后,他们从出生似乎就只配追求吃饱穿暖,但其实这样的追求有时也会成为梦想。书中所描写的冯歪嘴子,一夜一夜地打着梆子,在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窗户上糊满了黄瓜藤的房子里忙碌与休息。他就靠着自己拉磨、做黏糕的手艺维持着鼻腔里的那口气息,还善良地将黏糕送给幼年的“我”,也不反击别人的调侃嘲笑,却落了个媳妇无端被街坊议论,最后难产而死的命运。在七八月份乌鸦飞来的季节,送走了去世的媳妇的冯歪嘴子,与他的跛脚毛驴一起,“照常地活在世界上,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独自抚养两个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悲观绝望的眼神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也许比活在悲剧里更悲哀的是,被悲剧浸透了的人已经麻木的不觉得自己活在悲剧里,那个时代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悲哀。
在那样痛苦的年代下,女人显得更加痛苦。失去独子卖豆芽菜的女疯子,在公公婆婆迫害下死去的小团圆媳妇,仅因为说话声音大、长得高力气大就被邻舍指指点点、最后难产而死的王大姑娘……“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实实在在地感的到寒凉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带来了悲哀……逆来的,顺受了。”于是他们看着团圆媳妇被扔进滚烫的大缸求救时无动于衷,却在她昏死过去时为她流下眼泪来,所谓的拯救,也不过是泼一碗凉水,叫醒她,继续这场荒谬的闹剧。在那个几近夺走团圆媳妇生命的晚上,呼兰河和往常一样安静,那天以后,也没有人肯为她掉半滴泪。人们将自己遭遇的不幸一股脑的地发泄给处于弱势的女性,甚至年长的女性成为欺凌下一代女性的帮凶。萧红曾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书中也反复提到“我家是荒凉的”,真正荒凉的其实不只是“我”家,是那个时代,也是不断经历苦难的萧红的内心。萧红从出生因家里重男轻女而不被父亲、祖母喜欢,到成年后被父亲强行许配给别人,再到后来几经男人的背叛。她的性别使她亲身体验的痛苦,结合她所看到的呼兰河城里女性的悲剧,都在无声地映射并控诉着那个生活悲凉而女性处境更加悲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女性活在“传宗接代”等男权思想的压迫下,活在无声的卑微里,活在对苦难和活着的意义不自知里。
但它丑也许也没有多丑,丑的内敛压抑,是在特定时代下封建的产物。
三、萧红——用童年治愈一生的悲情作家
全书以“我”这个小孩的视角记录着呼兰河的故事,用纯真的语言描写悲凉复杂的那一方人间。文中总会读到“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所以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等等的天真语言。也许对于小小的“我”来说,和祖父一起躺在床上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在放杂物的房间里翻找稀奇的玩意儿当玩具,在后园的韭菜地里看蝴蝶,蚂蚱,蜻蜓,在院子里看天上变成各种形状的云,算是人生里的光吧。但文章的小孩视角中,又穿插着如“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么凄凉的夜”“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这样成熟沉重的成年视角评价。曾经有祖父陪伴的童年也许也是萧红一生不可多得的光,就像书的最后所写的:“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它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但也成了萧红成年生活的镜子,反射出更多的无奈与悲凉,刺痛萧红的心。
“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大地则满地裂着口。”萧红对童年回忆的起点定在了天寒地冻的严冬。大地的裂口毫无方向地延伸至几丈长,可能正如萧红那颗充满悲凉的支离破碎的心,无法愈合。萧红短暂的一生在潦倒、背叛与苦难中度过,一生漂泊,却有从未停止过反抗。她骨子里的韧性,她的洒脱与清冷,注定她的灵魂里,注满了北方凛冽而无所顾忌的冷风。在去世的前两年,她在潮湿的香港,写下《呼兰河传》,作为她一生的传记。我想那一刻,她与这世界、与自己的灵魂终于是平等而善意的,是自由的,在呼兰河历史上人们逆来顺受和抵抗厄运的复杂交汇之中,我看到了萧红这一浮萍最终的,尘埃落地,大器终成。
萧红一生的最后时刻在回忆童年中悄然逝去,也许与祖父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治愈着她一生少尝幸福而充满裂口的心;如今翻天覆地的时代,也许也在治愈着曾经被严冬封锁了的、满是荒凉的、裂着口的大地。